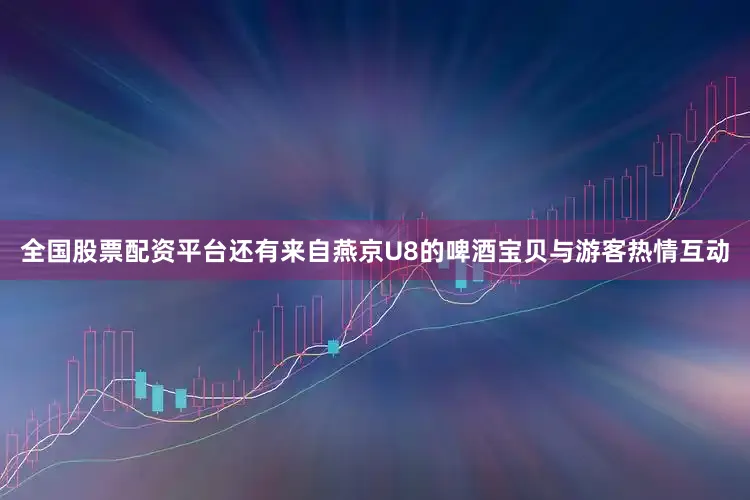2025年9月3日,长安街
一辆运输车上静静固定着一枚未曾对外披露的远程空射导弹——“惊雷-1”。
它的亮相并非阅兵场上的装饰,而是中国空基核打击力量从理论迈向实战的坚实证明。
全球军事观察界迅速认识到:中国已圆满完成了“三位一体”核力量的最后一项构建。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我国核威慑力量得以依托陆基与海基的双重支撑而稳固发展。
东风-41导弹拥有全球打击的潜能,而巨浪-3型潜射导弹则潜藏于深海之中,时刻准备出击。相较之下,我国空军却长期面临“名存实亡”的尴尬境地。
轰-6系列尽管历经多次升级改造,其核心平台依旧源自图-16的设计,航程受限,突袭能力亦显不足。
搭载的“长剑-20”巡航导弹,因其速度较慢且弹道固定,在遭遇现代一体化防空反导系统时,几乎难以突破其防御。
外界普遍认为,我国的“三位一体”实则演变为“两位半”的格局。
“惊雷-1”的惊艳登场,一举消弭了种种质疑之声。
中国有过空基核打击历史。
1967年6月17日,我国轰-6甲型轰炸机成功实施了当量达330万吨TNT的氢弹空投,从而跻身全球为数不多的具备空投热核武器能力的国家行列。
数十年后,能力停滞。
缺乏远程战略轰炸机,缺少高精度防空导弹系统,技术难关限制了发展道路。

直至2013年前后,国家战略需求促使技术实现重大突破——美国在阿拉斯加的格里利堡部署了GBI地基中段拦截系统,该系统专门用于应对来自北极方向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威胁。
若中国陆基导弹采取传统弹道飞行,其将极易遭受预警系统的探测、精确跟踪以及拦截措施的威胁。
必须开辟新路径。
“惊雷-1”项目启动。
精准打击:旨在瘫痪敌方至关重要的反导设施,从而为后续的核打击行动清除路径障碍。
果断摒弃亚音速巡航模式,我们毅然选择了“火箭助推—高超音速滑翔”的崭新技术路线。
这并非炫耀技艺,实则旨在攻克“如何在激烈对抗中实现可靠突破”这一关键难题。
在阅兵式上亮相的“惊雷-1”导弹,全长约10米,直径达到1.5米。其外壳涂覆了一层高光洁度且耐高温的特殊涂层,而前端则采用了轴对称的双锥体滑翔器设计。
此设计旨在应对极端飞行条件——在临近空间以20马赫的速度滑翔时,气动加热导致温度攀升至2000摄氏度以上,普通材料几乎瞬间遭受烧蚀。
滑翔器之表面积需抵御剧烈的热流冲击及压力梯度的挑战,同时确保其气动稳定性得以维持。
风洞实验持续验证了该设备在马赫20高速气流环境中的姿态操控性能。
“惊雷-1”型导弹配备了两级固体燃料推进系统。
首级将导弹推升至大气层之外,紧接着,第二级完成姿态的精确调整,随后释放滑翔器。

滑翔器穿越至大气层的边际,以类似“打水漂”的技巧,以超音速的速度翱翔。
该飞行器的最大速度可达到约20马赫,即便在飞行末段,仍能保持10至12马赫的高速。
它能够在中后段实施广泛的横向机动,进行俯冲变轨,甚至实现滚转规避。
现行的反导系统主要依靠弹道预测技术,然而,在遭遇此类非弹道、高度机动的目标时,拦截的机会几乎微乎其微。
提供两种滑翔器配置。
一款设计为双锥体形态,着重于末端的高机动性能,特别适用于攻击诸如地下指挥中心或导弹发射井等点状目标;而另一款则采用面对称的升力体结构,在中段能够实现广泛的横向机动,非常适合对区域目标进行覆盖。
此“一弹双型”的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了对于多样化作战场景需求的高度契合与深入响应。
该制导系统融合了中段惯性导航技术及北斗卫星的精准修正,而在末段,则转为采用主动雷达制导方式。
CEP ≤ 20米。
这表明其威力不仅足以摧毁地面设施,更能够精确锁定并攻击地下加固目标的薄弱环节。
该弹头的核当量介于20万至30万吨TNT之间,加之高超音速撞击所产生的巨大动能,其实际造成的破坏力显著超越了同等当量的传统弹头。
动能本身便是致命的附加力量——其高速撞击之力足以洞穿数米厚的混凝土,一举摧毁地下掩体。
载机为轰-6N。

这并非轰-6K的常规升级,而是一次深层次的改进。
最为显著的革新便是安装了空中受油装置,此举使得作战半径由原先的约3500公里大幅扩展至5500公里。
机腹配置了半埋式挂架,搭载一枚“惊雷-1”导弹,此举有效减少了飞行时的空气阻力。
自我国东北战略基地腾空而起,经过一次空中补给,轰-6N型轰炸机便能飞越至北太平洋高空,进而实施导弹发射任务。
“惊雷-1”的射程介于5000至8000公里之间,这一距离足以将阿拉斯加全域纳入其覆盖范围,乃至包括格里利堡的反导设施。
打击航线明确:轰-6N战鹰自东北空域腾空,飞跃白令海峡上空,抵达北极圈周边的发射区域。
导弹腾空而起,沿高纬度轨迹疾速飞行,其携带的滑翔器随后以超音速的速度猛然俯冲而下。
格里利堡的GBI拦截弹安置于加固型发射井中,其井盖的开启过程需耗时数分钟。
“惊雷-1”型号在末段冲刺速度迅猛,敌方几乎来不及做出反应——井盖尚未开启,拦截弹便已化为乌有。
此举一举摧毁了美国本土反导体系的核心环节,为东风-41等陆基导弹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
这并非纸上谈兵。
研制环节紧密相连。
自2013年项目启动以来,2015年便实现了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地面点火试验,其推力曲线表现出稳定特性;2017年,成功集成了北斗制导模块,并完成了抗干扰性能的测试;2018年,轰-6N平台完成了改装,机腹挂架结构通过了强度验证;2019年,进行了首次飞行试验,模拟发射与分离操作均顺利完成;2020年,尽管疫情肆虐,远程协同仿真工作也未受到影响;2021年,在马赫20风洞试验中,滑翔器模型表现稳定;2022年,精度测试结果显示,圆概率误差(CEP)达到了20米;2023年,进行了实弹挂飞试验,轰-6N携带弹药成功巡航四小时,系统运行全程保持正常;2024年,在高原雪地环境中,全系统经过验证,成功在零下30度的低温条件下发射。
试验数据超万次验证可靠性。

在此之前,我国曾致力于将长剑-20巡航导弹升级为核打击版本,然而,由于其速度较慢、突防能力不足以及射程有所缩减,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一尝试。
“惊雷-1”已全面切换至高超音速飞行轨迹,这一转变充分证实了其作为当前最为高效的突防策略的地位。
美国部署的萨德和宙斯盾系统在应对常规弹道或巡航导弹目标时表现出色,然而,面对高超音速滑翔体却显得力不从心——雷达的追踪速度难以跟上目标的快速机动,而拦截算法亦难以准确预测其轨迹。
国际反应迅速。
美国国防部已对阿拉斯加基地的生存能力进行了全面重新评估。
日本媒体纷纷公开发表忧虑之声,对东海地区的战略平衡可能遭受破坏表示深切的担忧。
尽管俄罗斯拥有被誉为“匕首”的先进高超音速导弹,然而,该导弹搭载于米格-31这一老旧平台上,射程受限,仅约2000公里,与我国轰-6N搭载的“惊雷-1”组合相比,实难相提并论。
这套系统对中国成本效益高。
轰-6N型飞机依托于成熟的平台进行升级改造,其生产线、培训体系以及维护网络均已完备,相较于新建陆基发射井或海基核潜艇,其成本效益显著,边际成本大幅降低。
尤为关键的是,轰炸机具备执行空中核巡逻的能力,能够始终处于战备状态,其生存能力远胜于固定的发射设施。
若轰-20未来得以投入使用,并配备新一代空射导弹,我国的战略打击力量将实现质的飞跃。
然而,目前阶段,“惊雷-1”已足以颠覆游戏规则。
具备打击能力。
经过更换标准弹头,武器系统得以实现对航母舰岛、指挥枢纽、雷达阵地等关键高价值目标的精确打击。

其卓越的高超音速特性赋予其在常规冲突中的“秒杀”威力——自发射至命中,敌方预警系统或许尚未及完成识别过程。
这种“核常兼备”的设计理念,显著增强了空军的作战灵活性。
部分人士对轰-6N并非隐身型平台表示质疑,对其生存能力提出疑问。
然而,应对之策早已融入作战架构:电子战飞机协同干扰,远程发射技术巧妙绕过防空区域,无人机诱饵分散敌方火力。
现代战争的本质在于体系的对抗,“惊雷-1”自始至终并非孤军奋战的兵器。
2025年9月,特朗普回归白宫。
不论谁主白宫,面对一个已全面实现“三位一体”核威慑实力的中国,每一次战略上的冒险都将需重新评估其潜在成本。
基于其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更显其可信度。
非软弱,实力之下的策略克制。
自1967年那震撼天际的蘑菇云腾空而起,至2025年长安街畔悄然无声的“惊雷-1”导弹,六十载的科技沉淀与战略定力,终凝成一把高悬于对手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它不事张扬,却潜藏着致命的威力;它不显山露水,却无人能够忽视其存在。
我国空基核力量至此已真正成形,这一成就非口号所能夸耀,而是源于我们扎实的工程实力、严谨的作战理念和坚定的战略决心。
个人配资,股票去哪里加杠杆,盈易点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